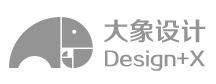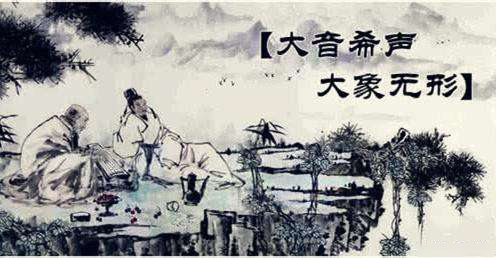
大音希聲,大象無形”為老子所提出,語出《道德經》,是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的一種美學觀念。“大音”是指音樂本身、音樂本源;“大象”是指形象本身、形象本源,都指向老子所說的世界本原—“道”也。“希聲”,并不是指沒有聲音,而是指人們聽不到聲音,“聽之不聞,名曰希”,“無形”并非指沒有形狀,而是指“視之不足見”。答主認為,老子的美學觀認為,藝術的真正意蘊是不能為試聽感官直接把握,它真實存在著,卻不是有形的藝術語言能表達出來的,需要審美接受主體以心境去感受,藝術作品的真正價值不在于語言層,亦不在形象層,而是超脫于藝術語言、藝術形象之外的意蘊層,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也~
(一)淺談“大音希聲,大象無形”之因
大音希聲,大象無形”追求的是一種藝術情感表達之最高境界的狀態,即“此時無聲勝有聲”的境界。為何會出現這種現象呢?答主認為這須得從老子的辯證觀去分析,正如喜極而泣、樂極生悲、靜中見動,真正的有韻味的藝術不是直白的表達,而是通過其他的反襯手段或者是“空白”來表現其至境,譬如“實景清而空景現”,這樣的表現手法更能凸顯出藝術的真實與神秘。
例如中國戲曲舞臺上一般不設逼真的布景,就是為觀眾提供想象的天地;中國書法講究布白,認為字由點畫構成,但點畫的人空白處同樣是字的組成部分,因而要求“計白當黑”,虛實相生,使得無筆墨的地方也成為妙境;再如白居易聽罷《琵琶曲《之后,欲予評價,卻道“此時無聲勝有聲”。
由此我們可以看出,藝術情感升華到一定極致后,直接的語言是很難將那種情感完全表達出來的,此所謂“言不盡意”也。所以,對于“大音”、“大象”這類接近心靈本源的東西,它客觀存在著,卻是無法完全貼切地將其表達的,需要以審美心境去觀照,所以才會出現老子所說的“希聲”and“無形”。
(二)藝術創作之“無為”
答主認為面對“大音希聲,大象無形”,在藝術創作與藝術接受兩個不同階段,是有不同的處理態度的。藝術家對于大音、大象時,想將其極致地表達出來,也許最好的表現方法不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探索、矯揉造作的捏造,恰恰面對這種極致情感的欲望迸發時,“無為“也許才是真正的“有為”。譬如瑞典著名演員嘉寶“無表演的表演”,看著心愛男子的尸體,這表現了女主人極度悲傷過度到麻木的程度,正是這種“無為”給觀眾傳遞了無盡的思考與心痛。藝術是反映生活,表達情感的,它源于生活,又高于生活,所以藝術真實不必在形式上追求與生活一致,反而其藝術意蘊恰恰是在追求“神似”上體現的。
(三)藝術接受之“有為”
接受美學的觀點認為,藝術作品存在一種“召喚結構”,藝術作品中布滿空白點和未定點,呈現為一種開放性的結構,這種結構本身隨時都在召喚著接受者能動的參與進來,銅鍋再創造將其充實、確定,使其得到具體化,面對希聲的大音,無形的大象,這時候就需要接受者去有為地填塞空白點、未完點,鑒賞者發揮想象力,對藝術作品進行再創造,當接受者與創造者發生共鳴的時候,便會產生一種心靈的審美愉悅;若一部藝術品通篇淺顯,一目了然,毫無內在意蘊,那么必然缺乏回味余韻,不值得去進行什么再創造了。
例如中國戲曲舞臺上一般不設置逼真的布景,就是為了觀眾提供想象的天地;中國繪畫也很重視留白,如南宋畫家馬遠擅長山水畫。畫山,常畫山的一角;畫水,只畫水的一涯,在畫中留下許多空白,讓觀眾去想象。
綜上所述,老子所說的“大音希聲、大象無形”乃是藝術追求的一種境界,大音非無聲,大象非無形,只是其外顯的聲、形不足表達其意蘊,所以便在藝術創作當中化為希聲和無形,其留下的空白便需要在藝術接受階段對其進行思索、填充、再創造,就如同鄭板橋先生所說的“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”,這也便是“空白”藝術引人入勝之妙處所在。